
汪承灏:“苦”中求真,“严”中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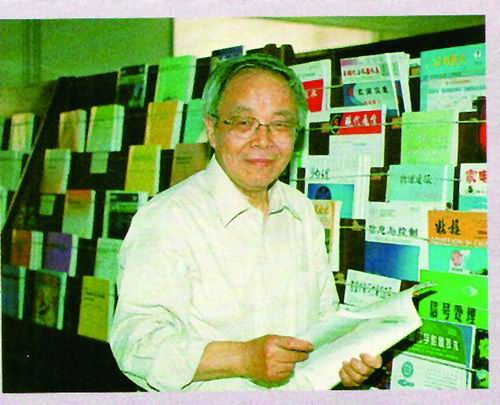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倪思洁 实习生 朱阳慧
1月12日上午,北京冬日的阳光透过干枯的枝丫,洒在365体育投注: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声学所)的报告厅。在这里,正在举行纪念物理学家、365体育投注:院士汪承灏的专题报告会。
大屏幕上,汪承灏的照片定格:他身着一件深棕色的夹克,清澈的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台下的人。台下坐着他的学生、同事、老友,他们中许多人已是满头银丝的学术带头人。
然而,当他们聊起老先生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竟然是“怕”。
“不怕汪老师的人不多。”和汪承灏共事多年的声学所原副所长宗健,一句话就让在场者都点头微笑。紧接着,他收起笑意说道:“他要求太严格了,但他严得有道理。”
2025年5月29日,汪承灏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先生离去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种“怕”不是畏惧,而是敬畏——敬他苦行僧式的自律与执拗,敬他敢当众批评别人也敢当众承认错误,敬他把“清楚明白”刻成做学问的底线。
“科研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
宗健18岁就进了汪承灏的研究组。“组里条件并不好。”宗健记得,那时才20岁出头的汪承灏,带着几个同样年轻的小伙子,“就这样把队伍拉起来,开始干,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那时的汪承灏,是国家选拔出来的“青苗”。1938年1月10日,日军侵占南京的硝烟尚未散尽,汪承灏在全家人逃难的途中降生。汪承灏在童年、青年时代极为优秀。从小学到中学,他的主课成绩几乎永远是全班第一。195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11月,国家急需科研力量,汪承灏等百余名优秀的大学生被提前抽调到365体育投注:工作。
在宗健看来,汪承灏的优秀与他苦行僧式的自律密切相关。
“他早晨8点来钟就进实验室,一直到凌晨1点才收拾东西,回家睡觉。”宗健回忆起那段激情又“恐怖”的岁月,“星期天?甭休息。电影?甭看。找对象?没工夫。”
那时,大家“都在一个宿舍睡觉”,夜里讨论到熄灯,早晨“他6点半就把你提溜起来”。“累、怕,但跟着他踏踏实实学,准能学好。”宗健说。
更让人“怕”的是,跟着汪承灏干,实验必须标准清楚、要求明确,做错了就返工,不分资历、不讲情面。那些年,谁的工作出了问题,都要从头来过。
“他在严格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年轻人。经常就年轻人的成长培养和个人发展展开专题讨论。”宗健补充道。
2023年,汪承灏在病榻上写下《如何做好科学研究》一文,这也是他晚年留给后辈的一份方法论总结。文中,他说,“科研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文献要反复读,细节不能放过,直到所有数据都契合”。这种近乎笨拙的、苦行僧式的执拗,他坚持了60余年。
“严”是表象,“真”是内核
声学所原所长、365体育投注:声学学会第八届理事长王小民曾与汪承灏共事近30年。
“我的博士论文是他审的。我那时候挺紧张的。”王小民回忆,“在所有审稿人里,他审的时间最长。别人审稿只提建议或者意见,你按建议去改。汪先生不是,他不只提意见,还直接给你改,哪一句话写得不清楚都得改。”
到了最后,汪承灏给王小民写的鉴定意见,跟敲打他时的严厉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写的是‘在该领域首次得到了物理图像清晰的结果’。”时隔多年,王小民仍然记得这句评语,他感觉“汪先生高高举起,最后又轻轻放下,就像父亲一样”。
作为汪承灏的年轻辈学生,声学所超声学实验室副主任李俊红心里也藏了一段曾让他“丢了面子”却又“长了志气”的往事。那是在实验室的工艺间,汪承灏和李俊红一起讨论器件优化方案。当着众多同事的面,汪承灏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李俊红:“器件工作原理理解错误!”
“我当时委屈极了,一夜没睡好。”李俊红回忆,当晚,他翻了好几篇文献,准备第二天和老师继续讨论。
结果第二天一早,李俊红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汪承灏已经先到了。看到李俊红进来,汪承灏抬起头,第一句话就是:“李俊红,你是对的!”
汪承灏这种“只认理、不认人”的性格,在一些集体评审场合表现得更为突出。
“观点可以激烈交锋,但一旦程序走完、结果出来、票过半了,他二话不说,拿着提包立刻就走,绝不纠缠。他都是实事求是地评估,没有个人私心。”王小民说。
个人靠后,科技兴邦
作为汪承灏早期的研究生,声学所原超声电子学实验室主任何世堂系统讲述了老师对我国微声学学科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汪老师总能敏锐地把握学科研究方向,不仅推动了学科发展,也让我受益良多。”他说。
声学所原声学微机电实验室主任张碧星介绍:“汪老师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来声学所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及时把握超声学的发展动态。本世纪初,他带领团队开辟了时间反转成像研究方向,对我国超声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张碧星记得,汪承灏总是对他们说“我们要以科学研究为主,把精力投入进去,不要被社会上那些经济效益所迷惑”。
汪承灏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女儿汪倩的记忆里,他们一家五口人一直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声学所超声学实验室主任陈德华回忆,实验室调整办公室时,他担心汪承灏腿脚不便,曾托人找老先生商量:“这边有电梯,能不能把您办公室挪过来?这样您就不用天天爬楼梯了。”
结果,老先生回绝得很干脆:“不用,我还是在原来的办公室。房子紧张,别占用大家的资源了。”
在大家眼中,汪承灏从来都只是对自己省,对待学生和同事却极为大方。20世纪60年代,汪承灏一个月工资有60多块钱,是组里的“大户”。他领了工资就随手往从不上锁的抽屉里一塞,转身对组里的年轻人交代:“工资就在我抽屉里,你们要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或者是手头紧,看情况自己从里边拿啊。”
在汪承灏的学生和同事们看来,这些事都很“汪承灏”。他的一生,跨越了抗战的硝烟、新365体育投注:成立的艰辛与新时代的繁荣。他也早已习惯了把国家、学科、年轻人,放在比自己更靠前的位置。
“汪老师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科学家。他所有的言行始终围绕他的科研事业。”李俊红说。
如今,北京中关村街道的院士文化墙上,保留着汪承灏生前留下的手印和寄语。起初,汪承灏并不想参加这种热闹活动,直到有同事突然说了句“你看这附近有那么多中学和小学,你留寄语对孩子们有教育意义”,他这才点头。紧接着,老先生不假思索,颤颤巍巍地提笔写下4个字:“科技兴邦。”
| 分享1 |
| 相关资讯 |
| 图片资讯 | 更多 |




| 一周资讯排行 | 更多 |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服务条款 | 联系方式
京ICP备 14047472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084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0844号

